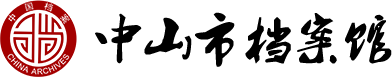|
在中国近代艺术的星空中,闪烁着众多香山籍的耀眼之星。但提到郑锦这个名字,不但对于一般的艺术爱好者是陌生的,恐怕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不少人专业士亦鲜有所知。然而,正是这位生前默默耕耘,身后萧条寂寞的香山籍杰出艺术教育家和画家,在20世纪之初,亲手缔造和发展了中国现代的第一所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国立北平美术学校,即当今名满中外的中央美术学院。
在中央美院寻找历史的痕迹,是件不易之事,从热闹非凡的王府井搬迁至朝阳区,那些属于央美旧时的记忆早已消失殆尽,就连仅存于王府井闹市校尉胡同里的中央美院美术馆,也被旁边的协和医院“吞并”,改建成协和医院的院史馆了。只有建筑的门楣上那一排白色的大理石雕画上,身着民国服装的男女青年,或手执画卷,或对着画板而作的画面,表明着这里曾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座学校的古老痕迹尚且如此破碎,关于一个人的记忆更是难以寻觅。原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杨先让曾经对媒体说:“我在中国美术界闯了半个多世纪,见得不少,但是也有很多该知道的还不懂。对郑锦先生也是最近几年才有所了解。虽然1998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建院80周年的年表上有郑锦的名字记载,但都是一提而过,郑锦何许人,为何能任学校的首任校长等等,一概不知道。如我者大有人在,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正因为这些遗憾,让我们有了追问的使命感。
●东渡扶桑获殊荣
郑锦是地地道道的三乡雍陌村人,因其村邻泉眼村有温泉,故号温泉居士。在清光绪的《香山县志》上,有其父郑玉池的记载。父亲是个开明的人,13岁的他便随父到日本横滨闯荡,入读当地由梁启超、鲍滔宗所创办的华侨学校————大同学校学习中文,跟随梁启超等游历三载,郑锦甚得鲍氏赏识,后还将其女鲍桂娥嫁与郑为妻。
1897年,郑锦在东京学习西洋画,中学毕业后就读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日本画科。期间,还考入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院,研究唐宋元明画法,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07年,郑锦以画作《娉婷》参加日本最高级别的文部省美展,这是第一位中国画人的作品首次被选入日本级别最高的美术展览,轰动日本华侨界,更为日本画坛瞩目。大正天皇为展览揭幕后巡视展场,当他见到《娉婷》这帧画作时,徘徊良久,被画中亭亭玉立、悠闲婉静的中国女性之美所吸引,不忍离去。翌日报章对此作出报导后,令日本全国对这幅画作充满了好奇。
然而,郑锦能震动日本画坛,并非只此一次。1912年他的力作《待旦》入选“大正美术展览会”,再为中国人争光。这帧画作获得日本画界及学者的称誉,考古专家黑川真赖博士说“唐代称为金碧辉映的技法,久矣湮灭无存,今于郑君画中复见之,当于东方艺道添一异彩。”之后此作还代表中国参展于“万国博览会”。
虽然他那惊世的巨作我们无法亲眼所见,但从一些资料图片上,我们还是隐约看到了《娉婷》古典的清雅————两位身着罗裙的少女并肩而立的景致,配以中国古雕花屏门等装饰,使得色彩明丽却并不花俏,而格子地砖的搭配,使中国古典女性的妩媚从画面上瞬间立体起来,可谓中西结合,匠心独运之作。
正是他出色的画艺,在1914年刚刚毕业的郑锦就收到了民国教育部一纸聘书,回国服务。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师。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在兼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文华殿古物陈列所所长时,首开先例,把每周更换的展品告知大众。这是把皇宫内的私家收藏公之于众,让文物开放,走入民间的第一步。
●创办学校为徐悲鸿争取留法机会
“我不管你们派谁去,但一定要有徐悲鸿在内!”这句话理应被记入中国现代美术史。因为这不仅显露出这个校长对抗强大潜规则的勇气,也是他为中国美术界培养人才作的最大努力。
1917年,在蔡元培的授意下,这个34岁的男人领命为国家建立一座国立美术高校。中国虽然一向以绘画见长,但从未有过正规系统的美术教育,多是师徒间口耳相传,这显然不是一个努力向现代化迈进的国家对待美术应有的态度。由于没有现成的先例,郑锦便远赴日本考察,从设立科目到授课学时,从后勤设备到教室采光,从教具增设到图书建制,在一年多的考察中,这个未来的校长殚精竭虑,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开创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
他本可以过上清闲雅致的生活,但他依然选择做一个校长。吸引他的,是时任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一番讲话:“注意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国第一所正式立案的 “国立北平美术专门学校”,于1918年4月15日成立了。郑锦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刚好这一年,他的第三女儿出生,为了纪念这有意义的年份,特别为女儿取名“美成”,可见郑锦对这所一手创办的学校何等珍重。
在他任上,经过一番努力,争取到六个公费去法国留学的名额。消息传开后,许多权贵纷纷举荐,一时间郑锦的办公桌上,放了十一位被“推荐”的人选。郑锦的原意是想把名额给一些有才能但又没有经济能力去留学的年轻人,为将来中国美术界培养人才,没想到事与愿违。最后,郑锦只有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说:“我不管你们派谁去,但一定要有徐悲鸿在内!”直到今天,徐大师的遗孀廖静文女士在给杨先让教授的信中还写到:“悲鸿当年每提到郑锦时,都称赞他为人正派。”
正是因为这种正派,令一些别有用心之人颇为悱恻,郑锦在外国生活了将近20年,对官场上的“为官之道”十分木讷,也不愿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去趋炎附势,不烟、不酒、不赌,自然会受到排斥,被人指为“高傲”,因而任校长8年后,被迫辞职。
然而在他任职在这段时间,学校培养了像刘开渠、李苦禅、李剑晨、常书鸿、王曼硕、雷圭元等一大批人才,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卓有成效的美术家或美术教育家。
●回归乡野推广平民教育
辞去校长职务后,郑锦一家人搬到河北定县,投入到由宴阳初、朱其慧等人创办的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平教会”)里,主持直观视听教育部。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在京城荣耀一时的校长,会作出去农村搞平民教育的决定,他来到农民中推广识字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公民意识,推介政府各项政策措施;收集民间传统艺术民谣和年画,加以提高整理。中国第一本专为农民而编写的识字课本 “千字文”,就在这时候诞生的。课本中4000多张插图,就出自郑锦的双手。
此外,他还创作、编著了以农民等平民百姓为对象的成人教育课本及教育挂图。他和同伴搜集民间绘画、编辑画范、绘制插图、幻灯片,修筑农村露天剧场,培训农民剧团。在定县,他制订了该县无线电播音台的全套实施方案,并自制出无线电台全部机器,如幻灯机、留声机等。还对该地区的民间音乐加以改良,融入教育性元素,以此启发民智。平教会是一个私人所办的社会学术团体,经费没有固定来源,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经费十分拮据。他就带领同伴大力节省开支,千方百计四处筹集经费。
与北京时的闲暇生活不同,此时画家的住处,是小村外一座荒废的瘟神庙。他把庙中的瘟神像作为装饰用品,将佛座改为金鱼缸,香炉变为大花瓶,庙中的石牌、烛台,也成了居所的自然雕饰,当地人因其不畏鬼神,故称他的家为“郑王府”。
他晚年因身体原因,返回澳门青洲山边石屋隐居,不问世事,以绘画自娱,直至终老,终实现了其一直渴望的单纯生活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