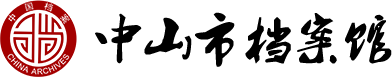
|
|||
| 【作者】中山商报 【文章来源】《中山商报》2008年4月21日 第 972 期 B4_B5版 【成文日期】2008-04-21 【点击率】3041次 | |||
|
余鞠庵,名潜,字通叔,号海棠花馆主、西横居士、矶边老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生于广东香山县(中山市)沙溪下泽乡,卒于上世纪末1999年,终年93岁。1918年考入隆都第一高等小学就读,初中毕业后,曾在县内小学当国文教师。课余潜心钻研书画篆刻、诗词。1933年加入广州尺社美术研究会。后师从赵浩公、卢振寰学习中国画。1937年石岐沦陷后,以刻印卖字为生。1958年筹办“六棉艺苑”至1966年结束营业,后退休在家。1983年被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吸收为馆员。数十年来,刻苦钻研诗书画印艺术。分别于1985年(中山)、1986年(广州美院)、1989年(广州集雅斋)三次举办个人诗书画篆艺术展览。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和省级展览,并多次被海内外媒体所介绍。其主要著作有《余菊庵书画集》、《海棠花馆印赏》、《海棠花馆吟草》、《鞠庵吟草》等。曾任中山市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虽然我和先生不是父子,但情同父子,早在30多年前少年的时候就跟随先生左右,学习书画。恰逢文革时期,正是我读小学的年代,那时候学文化的机会少了许多,加上当时学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教学要缩短,到广阔天地去锻炼的精神指示,所以在初中与高中的四年读书中,劳动与学习的时间差不多是相等的,特别在石岐一中读高中那两年时间,有一年是在学校的农场里度过。由于我喜欢涂鸦,从小跟黄剑培先生学画画,读书时也就更喜欢美术课了,后来在一中的老美术教师黄敏之先生的引见下得以与先生相识,从与先生相识那天到先生于 虽然,先生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但是,在跟随先生多年的岁月中,我日益感受到来自先生的精神品格的巨大感召力。值我市建设"文化名城"之际,将我所知道有关先生的一些往事述列出来,以作怀念。 逆境成才路艰辛 先生于清光绪32年(农历丙午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历 在石岐那段时间,先生曾一度进入粹存国文专修学校、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学习。后来为了学习绘画,先生于24岁那年即1931年到广州学习绘画,进入了关金鳌先生创办的美术会“尺社”,因此得到了关先生的指点,学习西洋画、素描。后来因生活所迫,为了生计不得不停止了在广州的学习,返回中山任小学教师,教授语文、英语、绘画,一教四年。在四年的教学生涯中,先生不忘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将工资除基本生活开支外,其余积存起来留作自己再赴广州求学之用。1937年三十而立的先生终于按捺不住对艺术追求的梦想,辞去教职,再次来到广州求学,到广州越华路择仁里由赵浩公、卢振寰两位画师创办的“山南精社”学习绘画。赵浩公、卢振寰两位画师以深厚的传统功力而名震南粤,先生在此学习期间,对北宗的山水和院体的工笔花鸟画技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广州学习这段时间里,先生同时以篆刻名家易大厂、邓尔疋为师学习篆刻,为自己的篆刻基础奠定了稳固扎实的功底。先生在几位老师那里不止学到了深厚的技法,也使自己的艺术素养、个人修养得到了极大的升华。由于先生勤学苦练,静心潜修学问,使先生在省城广州崭露头角,特别是书法方面为人称道。当时清代名臣沈葆桢之孙沈演公以及曾跟随孙中山的名将陈策曾为先生在报上刊登润例(见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第337页有记录),沈演公当时称先生的榜书“沈雄苍健,非时辈所及”。先生为求生计,只得为人写书以作生活补贴之用,当时求字者甚多,位于人民北路有一白宫酒店,其招牌就是先生所书。 然而好景不长, 筹办“六棉” 在1950年解放初期,政通人和、百废待兴。先生一家五口搬迁到石岐镇悦来路西横巷16号老宅居住,为了生活只能仍然用自己的特长来找工作,因为旧文人在那个时代难有用武之地,先生只有在石岐孙文西路设摊写字刻章,来维持生计。由于在这个百废待举的时代,对艺术不是那么重视,先生的生活也是难以为继。在1953年先生的妻子批准赴港定居,1957年长女洁婵亦赴港随母生活,先生与幼女留在国内,生活依然清贫。后来,先生的刻字摊纳入了“刻字合作社”,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单位挂靠,但先生体力不好、又有高度近视,工作起来很是吃力。没多久刻字社也因生意清淡,难以生存,被解散了。先生在近花甲之年再次成为社会失业人员回到家里。虽然生活清苦,但先生仍希望能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在上世纪60年代初,先生就已经当选为政协委员,而且还在 1961年,先生筹办过一间文物商店“六棉艺苑”,在中山也稍有名气。“六棉艺苑”是在1961年春成立。中山当时是没有文物商店,故此在一次石岐政协学习小组活动中,有委员提出:“其它城市也有文物商店,中山应该也有。”有人建议石岐应成立一间文物商店,后来得到当时的县委统战部及文教局支持,由先生与黄季骞、程十里三人筹办成立了“六棉艺苑”,选址在孙文路西山寺旁。由于经费困难,当时镇委知道情况后,主动拨出300元作为基金并派赵得君同志协助“六棉艺苑”展开工作,使“六棉艺苑”得以顺利开业。在此期间先生经常免费帮群众写一些家常文书和春联来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大约在1964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来石岐的时候,亦到“六棉艺苑”参观和购买法帖多部并留下墨宝,并予肯定。但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四人帮横行,“六棉艺苑”被诬为黑店,将文物当成四旧查封,所有文物全被没收。此时先生已近花甲之年,生活保障只有靠妻子及朋友的接济,生计才得以维持。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是非黑白颠倒的年代已成过去,先生又迎来了艺术的春天,文革时期已封之笔又重新执起,满怀创作激情的先生开始进入创作佳期。在拨乱反正后的1980年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征集活动中,先生的篆书对联作品“清心固为好,即事多所欣”经推荐有幸入选,展览结束后,所有作品收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成册,先生的作品位列广东第一。#p#副标题#e# 功力深厚诗书画印“四绝” 先生的诗、书、画、印被世人称为“四绝”,可见先生的功力深厚、格调高雅。 先生的诗,古朴纯真,毫不造作,率直、坦荡、平和、我邑诗人李浩先生在评先生诗风时说道:“句句是家常语,却字字扣人心弦。”这种感情真挚、平白无华的风格在先生的诗风中可以体现出来。如1951年所作的《岁暮别》:“岁暮别妻孥,仆仆胡为者。所冀在蝇头,宁复怀潇洒。炊烟笼寒庭,斜日明古瓦。老妻理行装,藤箧向邻借。稚女随我行,牵衣不肯舍。俯身哄以言,归去骑竹马。我往即当归,与汝糖盈把。一步一回顾,惘惘情难写。”先生一生中最为喜爱陶渊明的诗,先生故名潜,字菊庵。在写实的诗体中,先生最爱杜甫的五律,因此在陪伴先生一生中的诗集为陶渊明和杜少陵两册。先生的诗,字字出自肺腑,其真、其喜、其愁、其爱、其痛、绝无矫饰。在先生73岁晚年痛失爱女之时,也是将悲痛寄情于诗,《哭佩蘅》一诗是先生撕心裂肺、真情尽露之作:“出国回辞别,竟成永诀时。病瘳方一喜,凶耗又重悲。往事空追忆,苍天何不慈。魂归依膝下,洒泪向天涯。”(三女佩蘅幼随母居香港,慧而好学,高中毕业后,在港小学任教数年,旋旅游澳洲,今夏忽得恶疾,昏迷,送院抢救始苏,康复后出院尚能致书于予,详述近况,又岂料旧病复发,而与世长辞矣,终年仅三十一,伤哉。)李浩先生在评论先生的诗时曰“以自然之笔,写自得之乐;以白描之景,传至诚之心”。为使先生早期诗词能更好地保存下来,1984年先生的学生林伯骥、曾麟沛曾为先生编印过一本《海棠花馆吟草》。 先生的书,集各家之长自成一家。先生早期曾学《乙瑛》、《华岳》、《礼器》、《张迁》、《景君》、伊秉绶、邓石如等,结体上古拙奇趣,不急不躁,从容安详,高古雄浑,有大将之风。在篆书上先生得力于吴昌硕、邓石如、赵之谦等,上溯《峰山》、《泰山》、《琅琊》等石刻。其笔力刚劲筋韧,圆浑丰厚,先生之行楷兼收颜、柳、欧、赵、瘗鹤铭之精髓。先生之隶书,在深研汉碑的基础上,吸取邓石如、伊秉绶的结体与用笔,有伊秉绶的风韵又有邓石如的古拙。我们从先生1982年评书绝句十八首的诗中的其中一首:“曼生似是矜才气,纵笔离奇博俗夸。篆刻却教人下拜,大方落落自成家。”就可以看出先生对书学的深刻研究。 先生的画,继承传统又自成一格。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当代著名的美术理论家刘纲纪、华夏与先生素未平生,偶然见过先生的作品,大为赞叹,华夏甚至辗转托人代求先生作品收藏。我国著名词人夏承焘先生见到先生的水墨山水,欣然写下“和云流出空山”的词句。先生早期学过西画,后转学传统文人画,先生上追宋代工笔院体,下学元代四家,先生的用笔,条分缕析、笔笔着力,充分体现出先生深厚的书法功力。先生早期之干笔皴擦山水画风,润厚疏朗,凸现出一股清逸之气,如第一本画册的作品《秋间鸣泉》、《秋山泉韵》、夏承焘题款的《山水水堂幅》等。先生的胸怀、眼光极其开阔、开放。在师承古人技法的同时,他更重视师造化,做到了石涛说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先生足迹遍及名山大川,他游览写实、观察入微,胸中自有万水千山。先生以无限的热爱、饱满的情感去感受大自然之美和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先生还对前人大家也深入研究给予点评,如《评清初四名僧画》评八大山人的诗:“怆怀故国怜身世,哭笑难分世岂知。试看寥寥三两笔,中多泪共墨齐施。”先生在点评的同时,也吸收他们的技法为己用,故此先生晚期眼睛患白内障之故,视力模糊,但画风粗而不犷、气在笔力、韵在墨彩,因而浑厚华滋。其所作山水、梅兰菊竹乃挥洒自如,得心应手,古拙苍劲,沉雄浑厚,大有八大,石涛之风神韵味。 先生的印,是推崇鹤山的易大岸而宗师东莞的邓尔雅。从师自易大岸、邓尔雅、黄牧甫后,自己上追至秦印汉玺,兼收浙皖两派,再注入篆体入印,又得吴廷扬、赵撝叔之精髓,使先生篆刻自成一格,其刀法刚健、秀雅的气度中蕴含书卷之气,古朴端庄。先生在《自题印存》诗中写道:“始我操刀轻末技,及殚精力尚难工。雕虫岂作名山计,刻鹄真钦往哲风。玺玩周秦味其朴,派分皖浙孰为雄。若夫创异不宗古,小子才庸未苟同。”早在1986年,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工作的黄小庚先生,亦是先生早年的学生,他通过多年来不断收集得来的先生篆刻印拓,整理成册,编成一本《海棠花馆印赏》予以出版发行,关山月先生在看过先生的《海棠花馆印赏》的稿本时,欣然题上“雪坭鸿爪”四字,这恰恰是对先生印风的概括。后《海棠花馆印赏》一书成为“岭南印综”四册中的其中一册。 诗书画展美院引哄动 由于先生的艺术成就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的尊崇,高尚的品德受到人们敬重,1983年8月先生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受聘为省文史研究员。在1984年文史馆的一次聚会上,先生曾用诗《辞别文史馆兼谢款待》来表达对政府的关怀:“甲子岁将暮,邀来六日游。挥毫陪雅集,餐事荷殊优。到处涌新象,临归更恋留。关怀及衰朽,感谢党恩稠。”1985年6月正式成为广东省文史馆馆员,这也是对先生艺术成就的肯定与表彰。同年先生被吸收为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也是在这一年,在中山市政府及谢明仁书记的关怀下,先生的第一本画集《余菊庵书画集》终于出版。 安贫乐道“苍苍梅株深深山” 先生对艺术孜孜不倦追求,更注重精神的生活,对名利的淡薄和对物质的无求,使先生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艺术成就的不断提高并未为先生带来物质生活的改善,先生在当时的石岐镇悦来路西横巷16号的老宅里一住37年。在1981年先生晚年相依为命的女儿秋文也随夫出国而去,先生独自一人继续居于旧宅,只有在香港的长女洁婵抽空回来看看先生,简陋的老房没有卫生间,就算刮风下雨的天气,先生如厕也要到悦来桥脚旁的公厕,这对一个70多的老人极其不便。这样的清贫生活先生也无悔无怨、泰然处之,先生有一方常用印章“顺其自然”正是先生的人生哲学。 在这段时间里我常陪伴先生左右,先生喜爱郊游,经常安步当车,与好友罗振声、李泳棠、李浩经常漫步于郊野,一路吟唱、悠然自得,对大自然美好的景色流连忘返,体现了先生对新生活充满热爱之情。先生非常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在1981年74岁高龄还带着学生坐硬席火车到黄山、庐山、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一带采风,跟随先生的我怎也不觉得先生像74岁的老人,他精力充沛、思路敏捷、一路吟诗、勾勒写生,为后来艺术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但1984年先生足部关节炎疾病开始,痛风常常折磨着他,经常使先生足不出户,卧病在床,因为先生不想住院,幸得我市名中医陈伯衡先生每周都来一至二次为先生量血压、体检,经常风雨无阻为先生送医送药,减少了先生看病的烦恼。记得有一次先生病重要到医院住院,但先生足不能走,后来由陈伯衡、黎学松医生和我三人用藤椅将先生搬下楼送往医院。 到1985年,我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辞去工作报考广州美术学院,考进了美院的工艺系设计专业,辞别了先生,踏进了广州求学之路。离别之时先生即赋诗三首《送别路荆游学广州》:“此别虽云暂,中怀总黯然。增人离索感,多雨早秋天。”“平居偶不见,一日等三秋。待君学成后,重得与同游。”“高瞻嘉汝志,深造不辞艰。莫作登楼客,三年弹指间。”以作勉励。 1986年政府为了解决先生的住房困难,曾拨款1万元给文化局,由文化局来解决先生住房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迟迟未能解决。后来我父亲单位开始建宿舍,在李浩先生、我父亲与公司协商后将政府所拨之款1万元转给我父亲单位,用我父亲名义分得一套新房给先生。于是在1987年先生搬离了居住37年的老宅,住进了凤鸣路青云桥步云里25号的两室一厅新居,使我也能得以同住并照顾先生的生活。新居环境清幽雅静、远离闹市、与烟墩山塔遥遥相对,在先生《迁居》的诗中写道:“市声不到似荒村,寂寂新居日闭门。好是明窗资远眺,先安笔砚对烟墩。”那时候先生虽已过八十,仍每天挥毫作画,每每佳作。所以,我们在研究先生作品的时候,不难看出先生这段时间的作品可谓炉火纯青。 1992年后,85岁的先生家人开始从海外回来看望先生,当时谢明仁书记得知情况后,了解知道原居地方不大,故此在湖滨路36号基边新村政府解困房中分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新房给先生,同时将原单位分的那套房子退回给政府。由于得到政府的照顾,先生的晚年也过得更加安稳,其《乔迁呈党委》诗中写道:“我为择邻处,迟迟未定迁。欲寻摩诘侣,同泛米家船。新居颇宽敞,风光亦丽妍。杜怀千万厦,惟党践其言。” 在先生的个人品格、思想精神方面,一直保持着君子般的坦荡荡胸怀,内心无比仁厚、宽和、正直、坦荡、豁达、纯朴,无论自己在身处逆境与遭遇不幸的时候,先生都能处之泰然,内心是那么恬静与坦然。他始终将艺术作为自我的终身追求,而不会视之为利禄工具。先生淡泊名利、守得清贫,所以在品读先生作品的时候,绝无“俗、甜、邪、霸”的恶习。对学生的教育先生更是注重德行,要求学生做学问先做人,从先生留下《论画示门生》的八首诗中的第一首是这样写道:“前贤作画志终身,耐得辛勤耐得贫。默默不求时辈誉,飘飘风格出人群。”该诗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先生崇高的思想境界。在我敬佩先生艺术成就的同时,更加敬佩先生的高尚品格。曾有很多人写过评论先生的文章,但是,我特别喜欢林墉先生的一篇短文“苍苍梅株深深山”,该文对先生没有过多赞美之词,而是对先生为追求艺术而清贫一生所发出感叹。 时至今日,我始终一直牢记着先生的教导,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虽然,我不能为先生做些什么,但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先生的艺术成就和高尚的品格,使我们领略到先生深厚的笔墨功力的同时,更能以先生作为一面镜子,为世人学习的榜样,也使先生的艺术精神得以延续和发扬。 最后我以先生喜爱一生的陶诗中其中一句作结尾来表达对先生的怀念: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