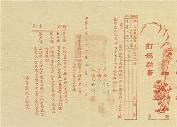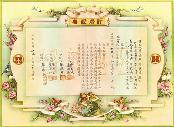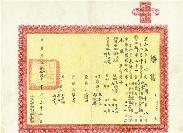|
古往今来,结婚从来都是人生大事。作为人生大事的记录与见证,结婚证(婚书)承载的不仅仅是个体的人生故事,它所蕴涵的历史印记,更是清晰地折射出社会政治经济、民风民俗的发展变迁,记录了时代的文明进步。
近日,市档案馆收藏了一批从清末到上世纪70年代的结婚证。这些或古老或现代、或精美或粗糙、或简洁或繁琐的斗方故纸,在甜蜜喜庆的形式之下,展现着一段段波澜壮阔、迂回曲折的历史场景,令人回味无穷。
清末:民间行为华丽文章
此批藏品中年代最为久远的,是一张“大清宣统二年”(1910年)的订婚书(图1)。婚书由大红色纸从右向左折叠而成,展开后长近一米,底衬翠绿色带暗花的色纸,虽历经沧桑仍不失精美。婚书封面印有祥云、花草与人物等图案,图案中间嵌有“文定厥祥”四个字。《诗经大雅 大明》中有“文定厥祥,亲迎于渭”之句,意思是说周文王通过占卜确信婚事是吉祥的,于是到渭水之滨迎娶佳偶。据南宋大家朱熹解释,“文”就是“礼”的意思,“祥”即“吉”,就是卜婚得吉后“以纳币之礼定其祥”。由此可见,此为订婚文书。
立婚书者为山西省心源县的杨承祥,他为自己的侄子与某前辈的孙女订立婚书。婚书用毛笔手书,内容丰富,达一百多字,字迹端正美观,词藻华丽优美,对仗工整,谦恭有礼,尽显古汉语的魅力:
“……尊慈不鄙寒微过信,冰言允以令长孙媛与仆舍侄结为百年佳偶,久切殷怀,适惬素愿。居连里闬声华未齿于崔卢,势隔崇卑匹敌敢当乎秦晋。杞梓淹金华之美,蒹葭得玉树之荣。想淑孙媛闺顺多仪堪媲咏絮之姿,愧舍侄庭训未习有忝题糕之能。虽曲礼三千隆于好合,须纯白五两用以将诚。昌卜五世,庆洽三生。恭惟仁慈海涵,鉴纳不宣……”
整张婚书没有出现将要结婚的男女主角的名字,只有双方家长的交流,充分体现了古时婚姻“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强势。婚书上没有任何官方的印记,纯粹是民间行为。
边区: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在这批结婚证中,最稀有的当数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的涉县政府发出的第29号结婚证(图3)。涉县,是位于河北省的革命老区,在抗战时期,因刘伯成和邓小平运筹赤岸、八路军一二九师鏖战太行而名垂青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新华广播电台、新华日报社等110多个党政机关单位曾长期驻扎于此。1947年,正值解放战争,边区经济条件非常艰苦,这张结婚证的粗糙纸质和简陋印刷就足以证明。结婚证书能够在这种条件下留存至今,实属不易。
1942年5月,晋冀鲁豫边区颁布了《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对结婚、订婚、离婚做了详细规定,强调了婚姻自由、平等的原则,这些都明确地反映在结婚证书上。证书用了整整一半的篇幅,摘录了《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四章关于“结婚”的内容,包括结婚须男女双方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男不满18女不满16不得结婚;结婚须向村级以上政府登记并须领取结婚证明书;直系血亲、直系姻亲及八亲等以内的旁属血亲不得结婚;患有精神病、花柳病及遗传性恶疾者不得结婚;寡妇有再婚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并不得藉此索取财物,寡妇再嫁时可带走本人的财物。而证书上的结婚誓词,也是强调男女双方“情感融洽,心意相投,在双方自愿原则下定立婚姻”,结婚后“夫妇均应互助友爱,共同建立平等自由幸福之新家庭生活。”
由此可见,边区确立的婚姻制度,树立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文明观念,着意解除几千年来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对建国后颁布的首部《婚姻法》的制订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有意思的是,边区人民政府的结婚证书与订婚证书配套(图4)。订婚证书上摘录了《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二章关于“订婚”的内容,规定订婚双方要自愿,别人不能强迫;男不满17女不满15不得订婚;订婚时男女双方均不得索取金钱财物;订婚时须向村级以上政府登记方为有效。两个证书显示,同为18岁的李年(男方)和刘英(女方)于1947年7月6日订婚,地点是一区,8月2日结婚,地点是二区。两证书均有结婚人和介绍人的指模,还盖有公章,说明当时的婚俗里,订婚不单是民间的风俗,还受到边区政府的承认和保护。
建国:法定要求由繁至简
建国初期的婚书中,仍然存在订婚证书,但已没有了官方的印记。如北京市的徐男与萧女,于1950年2月21日订婚,立下了非常精美的订婚书(图4)。由鸳鸯、喜鹊、荷花、百合等喜庆吉祥图案组成的彩色订婚证书有固定格式,内容除了订婚证言、祝福语外,就是订婚男女的姓名、籍贯、年龄、订婚时间以及介绍人、主婚人、证明人的姓名和印章,完全看不出有政府管理的痕迹。1950年10月25日,两人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第四区公所领取了京婚四字第884号的结婚证书,区政府的大红印章端正地印在结婚证书的时间落款上。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该法明确废除包办、强迫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结婚男女双方应亲自到所在地(区、乡)人民政府登记,凡符合法律规定的,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即发给结婚证。这是中国首次将结婚登记作为结婚者的法定权利和义务而加以规定。1980年9月和2001年4月,《婚姻法》进行了两次修订,均重申了婚姻登记的要求。
随着《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与修订,无论是内涵还是形式,结婚证书变得越来越简洁明了。内涵上,有关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等内容逐步消失,突出了“自愿结婚”、“经审查符合婚姻法规定”等内容。形式上,随着法制的健全,结婚证的作用和使用频率逐步加大,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长期沿用的单张“奖状”式的结婚证书,改为手掌般大小的簿册形式,更便于携带和保存。2004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使用新版婚姻登记证书,更便于计算机打印、安全防伪和今后的联网查询。
民国:
结婚———官府纳税
登记———悉随尊便
据介绍,民初的婚书是在店铺里购买印制好的空白证书,填写之后贴上官府规定的印花税票就算得到承认。本批藏品中一张1928年的婚书,大红纸上印有烫金花纹和“文明结婚证书”几个金色大字,右上角贴着四张面值为一角的国民政府印花税票。但婚书上只出现家长和介绍人的名字,仍然没有主角———结婚男女的名字。
1929年起,南京国民政府陆续公布了《中华民国民法》的五个篇章,其中《亲属篇》于1930年12月6日颁布,1931年5月5日起实行,规定了因婚姻、血缘和收养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虽然《中华民国民法》仍保留了不少封建婚姻制度的内容,如肯定了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其他封建习惯,规定“未成年之男女订定婚约,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允许父母在子女未成年时便为其定下终身等等,但它毕竟对传统的婚姻制度有了很大变革,至少从这个时期的婚书上看,转变是巨大的。藏品中一张1937年北平市(北京)社会局印制、警察局发行的结婚证书(图2),除了有结婚男女双方祖宗三代(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的姓名外,在显要位置记录了结婚男女的姓名以及年龄、籍贯等在现代人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情况,突出了结婚人的主要地位。
《中华民国民法》虽然有专门的章节讲婚姻,但并无规定必须进行强制性的统一的婚姻登记。据《广州市志》资料显示,广州自1930年6月开始在市社会局设立婚姻注册登记,整个民国时期(不含伪政权时期),全市注册登记结婚的仅736对。
结语
一纸婚书,浓缩着沧桑世事,见证着社会发展。也许今后,婚书还会适时“变脸”,我们相信,它的每一次改变,将意味着我们的法制更加健全,我们的文明更加进步,我们的科技更加发达,我们的民族更加振兴!
|